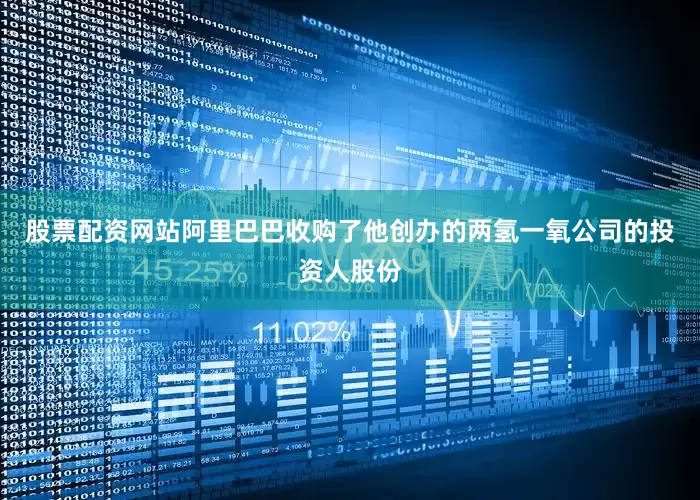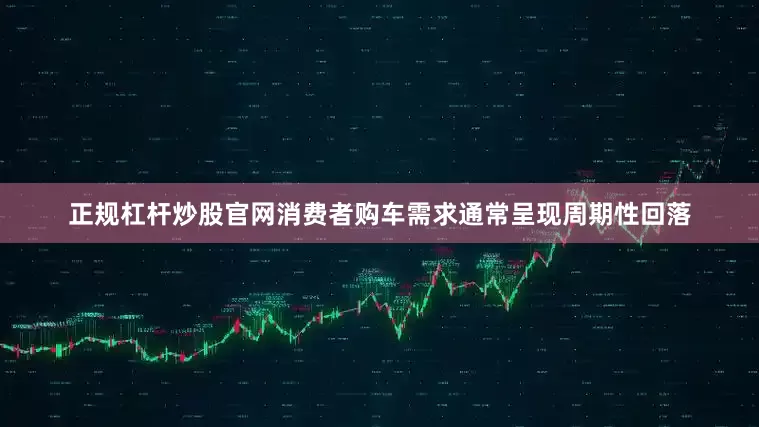漫步于首尔的街头,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时间错位感。在地铁站的指示牌上,汉字清晰可辨;而在化妆品商店中,“美白”、“保湿”等熟悉的方块汉字,犹如置身于自家的巷弄之中。
然而,一旦将视线转向三八线北方的平壤,眼前的景象便会截然不同。这座城市宛若一片谚文的汪洋,从标语到招牌,无不充斥着密密麻麻的圈圈杠杠。即便是古老的建筑之上,汉字的痕迹也几乎被彻底抹去。
真令人不解。半个多世纪以前,半岛的南北两侧曾约定共同与汉字“决裂”,都致力于打造一套纯粹的民族语言。然而,时至今日,一方却让汉字悄然“回光返照”,而另一方却将其深埋,近乎完全遗忘。
千年情仇,一朝断情。

汉字,自古便是这片广袤土地上无可争议的霸主。自汉武帝设立乐浪郡以来,它便成为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独占的书写载体。无论是高句丽王陵的石碑铭文,抑或是李氏朝鲜向大明皇帝呈递的奏章,皆以汉字为记。
昔日,若能挥毫泼墨,书写出一手娟秀的汉字,便如同现今能够流畅地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一般,成为身份与学识的标志,其脸上便自然而然地刻印着“高级”二字。
于是,在1446年世宗大王发明谚文之际,整个朝廷陷入了极大的动荡。众多大臣竭力抵制,他们的反对理由相当实际:我们学习中华文化,采用汉字,这样才能彰显高雅,这所谓的“本土之物”究竟有何价值?难道这不是在降低我们的身份吗?
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鄙视观念,使得谚文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始终被冠以“谚文”之名,意指“俗人所用之字”,专供妇女与儿童识字所用,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。

甲午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一个转折点。大清国遭受败绩,“中华中心”的光辉瞬间黯淡。紧随其后,日本人的到来,以一连串的组合攻势,将半岛的文字环境搅动得翻天覆地。
殖民者初期曾推崇谚文,声称其“助力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”,然而不久便反其道而行,强制推行日文与汉字混合的“同化教育”。直至1945年光复,无论南方抑或北方,新成立的政权均达成了共识:欲求独立,必先摒弃这些纷繁复杂的“外来符号”。
一左一右
1948年,随着南北分裂,一场波澜壮阔的“去汉字化”运动在两地同时掀起。然而,两者的实施方式,却是相去甚远。

在朝鲜,金日成的立场堪称坚定。他明令禁止,报纸、教科书、官方文件中不得出现任何一个汉字。若民众继续使用汉字书写信件,甚至可能被冠以“思想守旧”的罪名。
与汉字一刀两断,彻底摒弃外来文字。
韩国的行事风格显得尤为“微妙”。1948年的法律规定,公文必须使用谚文书写,然而巧妙地留下了一道门径——“在必要时,括号内可标注汉字”。进入70年代,朴正熙政府表面上施行铁腕政策,禁止小学教授汉字,但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仍可选择选修。
报纸的头条非得用谚文不可,然而当你翻阅至内页,却发现广告上“大特卖”三个汉字,其印刷之大,几乎无人能出其右。

为何差异如此之大?归根结底,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。当时韩国社会,各派势力错综复杂,支持汉字的老派知识分子依然存在,而新兴的商人发现用汉字进行广告宣传更为有效,普通民众在举办喜事或收取礼金时,若礼簿上不用汉字记录名字,总觉得不够完整。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,想要一蹴而就地进行改革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谁才是真学霸
瞧这里,你或许会想,韩国街头随处可见汉字,那么当地民众的汉字能力肯定远超朝鲜吧?然而,事实却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
尽管朝鲜在公共领域对汉字实施了所谓“焦土政策”,但在教育领域,其并未真正放松对汉字的传授。1968年,金日成明确表态:“鉴于南朝鲜的出版物及我们过往的书籍中仍大量存在汉字,为了确保人们能够阅读理解,汉字教育仍需继续。”

此言一出,“汉文”课程立刻重返高中必修课的行列。
现今的朝鲜学子,传闻自小学阶段便开始学习汉字,而高中毕业后,他们需掌握两千个汉字。若欲就读大学并攻读历史、法律等学科,还需额外掌握一千个汉字。一位脱北者曾言,他们的手机中皆装有汉字词典,每当看到谚文“사랑”(意为“爱”),脑海中便会立刻浮现出对应的汉字“愛”。
进入2000年,一项调查显示,在首尔的高中生中,能够正确书写“韓国”二字的人不足半数。
时下,年轻人往往难以解读爷爷遗留的日记,而历史系的学生在钻研古籍之前,亦需先行报名参加汉字补习课程。这种现象已然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。

此刻,韩国社会陷入了动荡。2011年,政府计划将汉字重返小学课堂,此举引发了家长们的激烈争议。一方愤怒地斥责:“学习汉字便是忘却根本!”而另一方则反驳道:“若让孩子连祖先传承之物都无法辨识,那才是真正的忘本!”最终,这一事件以折中方案收场:教材中加入了汉字注释,而是否学习汉字则由学生自行决定。
避不开的同音魔咒
归根结底,无论政策如何变幻莫测,一个不争的事实是:在朝鲜语中,高达七成的词汇源自汉字。这条纽带,即便想要割舍,也难以断然分离。
那就是同音词过于繁多。“의사”(uisa)一词,既可以指代“医生”,也可能代表“义士”。“원수”(wonsu)同样如此,它可能意味着“怨仇”,亦可能指代“元帅”。在日常对话中,我们尚可凭借上下文进行推测,但一旦涉及签订合同、制定法律等正式场合,问题便会变得复杂起来。

韩国民众最初便遭遇了此类纠纷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一场著名的诉讼案引发了广泛关注:两家企业在签订合同时,因关键词“대리”(daeri)未标注汉字,一方坚称其为“代理”,而另一方则认为是地名“大里”。这场诉讼历时三年,最终尘埃落定。
自那以来,在各类法律文件与重要文献中,于谚文词汇之后附上括号内的汉字标注,已然成为韩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。
朝鲜是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的?解答直截了当:通过教育,通过机械记忆。由于全国人民都曾在学校接受过汉字的系统学习,因此当他们看到“문제”(munje)这一谚文时,大脑便会自然地联想到“问题”;遇到“정치”(jeongchi)时,也能迅速辨识其为“政治”而非“整治”。
汉字虽不常见于街头巷尾,却宛如一部“隐形字典”,深深烙印在每个朝鲜人的心间。

结语
文字的挑选,远非单纯的技艺考量,它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一个民族渴望成为的肖像。
朝鲜所选择的路径,正是对一种极致的“民族主体性”的追求。历经多轮外来文化的冲击,该国迫切需要一种“纯净无瑕”的标志来彰显其独特性。因此,他们毅然将汉字从公共生活中驱逐,却又悄然将其纳入教材之中。这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双重策略:既保留了“我们只使用自创文字”的尊严,又满足了“我们能够理解历史”的需求。
当需要时,便将其应用于实际,而在无需时,则将其置于一旁。

今日,朝鲜的一名大学生或许能够熟练地朗朗上口《论语》的汉字全文,但在手机上输入汉字的能力却未必得心应手。相较之下,韩国的一名中学生或许连“韓”字都难以书写,却能自如地运用各种网络流行语,与全球的同龄人畅谈无阻。
一项将汉字深植于教育的根基,另一项则将汉字保留在生活的表层。这两条道路看似背道而驰,实则都在探索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:一个民族如何在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外来之间寻找到自身的定位。那些在半岛若隐若现的汉字,正是这场悠久角逐中最可靠的见证。
#新作者流量激励计划#
杠杆股市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